山西煤老板,一个本不该诞生的悲情群体
煤老板们不是神,也不是魔鬼。尽管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群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损害远大于贡献而不招人喜欢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一个将来在历史上注定会留下负面影响的时代概念,但实事求是说,所有的谴责和谩骂不能只朝向他们,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替罪羊,是上帝不小心造出来的一众孙小猴子,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前瞻性的理性和没有科学规划的体制所孕育培植出来的一个怪胎而已。

《老苏》和《小经历》(见《天下农人》,鲁顺民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9月)是鲁顺民先生为数不多的描写山西煤老板的两篇纪实之作。两篇文章写的是同一个人,即曾是岚县首富的老苏,前者是作者眼里的老苏,后一篇是作者整理后的老苏口述实录。二者其实可以当做同一篇文章的上下两篇来读。
按作者的说法,“老苏是一个煤老板,是那种在山西各县都能找到的煤老板……他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至少山西农民企业家在1979年之后30年走过的人生之路”(第40页,同上)。譬如,老苏和大多数煤老板一样,都是在1980年代国家“有水快流”的政策鼓励支持下,联合村里一些人一起大胆走上了挖煤卖煤的道路;在起步的时候也都是只筹集到几千元钱,而后靠几万元的贷款就大干起来;在经营过程中,同样是是历经坎坷,受尽磨难:煤炭形势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到处躲债,以至于好几个春节都不敢在家中过。而他挣了大把的钱的时候,一些过去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和政府就不断地向他伸手,向他索取,他也不得不屈身于那些已退或未退的官员护翼之下,“在办公室看到许多工作人员,不是这个局退下来的局长,就是那个乡镇退下来的书记,就连给他开车的师傅,都是若干年前县委书记的司机” ;企业有了利润,他也像其他煤老板那样,会慷慨地拿出其中一部分,给村里打水井、修公路、植树造林……就连他们最后的身份变更也都是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先是优秀企业家,而后就是当地政协委员、党风廉洁监督员……
就是这么一个虽吃尽百般苦头,后来表面上总还是风光无限的人,最后却在63岁时死于癌症,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早在十几年前,老苏就在医院检查出了糖尿病,他说:“10年中间,挣了一些钱,也挣了一身病,进入2000年,就住了两回医院。什么病?糖尿病。血糖高出数值几倍,凶险不凶险!现在每年春夏都得住半个月医院,不然坚持不下来,日日打胰岛素。”
老实说,看到老苏这样一种人生结局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很不是滋味。这让我想起了老苏身处其中的那个煤老板的特殊群体。不说他们那种几乎一模一样的惨痛经历,单就最终归宿那刻而言,竟都是一场相似的令人扼腕的悲剧。前半生拼死拼活用健康换钱,后半生身体过早透支,用钱来换取健康。仔细想想,过度的心力交瘁和煤矿上污浊不堪的空气,实际上早就给他们的生命提前划上了句号。1991年夏天,我曾以《山西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临汾市河底乡一矿和二矿蹲点调查,当年接待过我的赵、张两个矿长后来也都是死于癌症,其年龄都只有50多岁,而另一个姓杨的副矿长则由于长年累月地在矿下劳作,年仅48岁就在癌魔的侵蚀下,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表面上来看,老苏他们这一类煤老板的人生结局,相对而言还算是不错的,毕竟也算得上是“功德圆满”“寿终正寝”了。作为煤老板的另外两类可能就更悲催了。一类是因开办煤矿赔了大钱,或者是遇上死伤事故,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要么是逃之夭夭,四处躲避;要么是心生绝望,一死了之。还有一类是煤矿做大了,想用资本绑架政治,给自己寻找更大的舞台,于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祸国殃民,无恶不作,以至于最后只能是锒铛入狱,铁窗悔罪。这一类人臭名远扬,可能更广为大家所熟知,比如原山西金业煤焦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新明、原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原山西大土河焦化公司董事长贾廷亮、原山西中阳钢铁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原山西离柳焦煤集团董事长邸存喜,等等。在这两年山西官场塌方式的腐败窝案中,这一类煤老板的影子几乎是无处不在。山西省省省长李小鹏就曾对外公开宣称: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出现了煤老板,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煤老板们不仅仅是由于经营煤业毁坏了自己的身体和可能熠熠发光的前途,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近乎疯狂的掠夺式开采,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污染了山西的自然环境,破坏了山西的生态平衡。
早在1990年代初期,我下乡去搞小煤窑调查时,时任《山西煤炭报》副刊部主任的李仑先生就曾经给过我一份山西省煤管局发给媒体单位的公开资料:根据山西省煤管局的综合分析,山西乡村煤矿采区回收率只有15%-20%,如果按1990年生产11555万吨计算,全年共动用734亿吨工业储量,也就是说,每采1吨煤,就要丢失毁坏近65吨的煤资源,相当于缩短了矿井寿命的3/4。全省乡村煤矿经批准的储量达277亿吨,倘按1990年115亿吨生产规模,按采煤区回收率达50%计,可供开采120年;如果按当时平均15%计,只能开采36年,服务年限整整要缩短84年!
这还说的是办了正规手续的乡村煤矿,可想而知,那些偷着干的小黑窑又是怎样肆无忌惮地在毁坏着国家的资源!1985年以前,由于各种体制的不健全,中央在号召大力发展个体、乡镇企业时,曾提出“有水快流”的口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不少人便适时地把发财致富的眼光盯在了煤炭资源的挖掘上。那时尚没有制订出《资源法》以及有关的管理条例,开窑口县里审批即可,更糟的是县一级管理也不成系统,胆大、没资金、没设备的人连必要的手续都不履行,便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加上山西很多地方,煤层浅,煤质好,见效快,于是一场无秩序、无计划、哄抢煤资源的大战就在山西各煤区拉开了序幕。只1985-1987年两年间,山西各地各种“三无”小煤窑就达1万多个。
这些窑口大部分没有足够的资金,只能因陋就简,东一锹,西一镢,把个好端端的煤炭基地弄得一塌糊涂,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浪费、被毁弃掉了。1991年9月,我曾到乡宁、蒲县等地跑了一趟,在那里只吃了一点煤便被报废的老矿口随处可见。每个坑口周围都布满了煤渣黑土,乱石满地、野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
滥挖滥采的结果是85%-90%的煤资源毁在地下而不能开采使用。何止如此!1990年代,山西每年还有相当的库存煤卖不出去而发生自燃,仅1991年,山西库存煤就高达7500万吨。
山西煤炭,经过几十年混乱无序的超强度开采,一方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日渐枯竭,另一方面是采空面积和被毁坏的土地俯拾即是。那些隐伏在地底下的采煤巷道横七竖八,纵横交错,很多高速公路、企业厂矿、农民房屋都是悬空而居,危机重重。据山西发改委统计,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区已达到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西1/8的国土面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早两年提供的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结果显示,全省因采矿活动引发的崩塌、滑坡有754处,影响面积14万亩;地面塌陷多达2976处,影响面积100多万亩。仅2010年因矿山开发导致的地面塌陷及采矿场破坏土地就达20.6万亩,其中12.99万亩是耕地(高勤荣《山西:比矿难更可怕的是地陷》,见高勤荣新浪博客)。人口只有3000多万的山西省,就有300万人因煤窑采空而饱受无妄之灾,几乎处处都有“鬼”村。
煤老板们的私挖滥采,导致山西的环境几被破坏殆尽:绿茵茵的山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岭,清亮亮的小溪变成黑乎乎的浊流,千年流淌的汾水早就断流,甚至那像一匹不羁的骏马滔滔奔流的黄河,现在也只能无力地发出病态的呻吟。天上呢,难得看见一太阳,满目都是灰茫茫的雾霾,吸进肺里的总是一股永远去不了的焦糊臭味……
煤老板们饱受人们指责——很多人甚至视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洪水猛兽,但客观而言,他们并不是那样没有良知,那样穷奢极欲,那样唯利是图,他们也经常处在一种矛盾和纠结的痛苦中,处在一种良心谴责的愧疚中。鲁顺民先生笔下的那个老苏就说:“我常想起我爹当初劝我的话,说开煤矿损阴折寿。这句话让我结记了几十年,当作鞭策和警示……开煤窑,牺牲资源,确实有些过意不去。”正是由于这种愧疚,煤老板们一旦有了利润,都会多多少少地拿出一些来反哺农业,感恩乡亲,回馈社会。老苏说,他光给村里打水井就打了三回,每回都至少要扔进去四五十万元;给村里修路和植树造林的款子也是他的矿里出。另外,每年还给村里每亩地补足230元,每人每年送1袋面、6吨煤……可以想见,这是绝大多数煤老板都具有的人性善性的那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煤老板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这种“虎口拔牙”的营生,所以侥幸成功后——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别人几辈子,甚至几十辈子都挣不来的财富,这种云泥之别的落差,必然催发他们及时享乐和人前摆阔的畸形思维,也因此在十几年前全国煤炭形势一片大好时,就有了一个山西煤老板在北京一口气买了109套房子的“传奇”,就有了2012年《天下被网罗》节目里“山西煤老板:我们需要飞机代步”的“神话”,就有了山西富豪邢利斌在三亚一豪富酒店7000万嫁女的疯狂举动……
煤老板们不是神,也不是魔鬼。尽管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群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损害远大于贡献而不招人喜欢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一个将来在历史上注定会留下负面影响的时代概念,但实事求是说,所有的谴责和谩骂不能只朝向他们,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替罪羊,是上帝不小心造出来的一众孙小猴子,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前瞻性的理性和没有科学规划的体制所孕育培植出来的一个怪胎而已。
他们本来就不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如前所述,1980年代初期,中央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水快流”,山西省委省政府机械地、片面地照搬照抄,而没有考虑到山西煤炭资源的特殊属性,反大力鼓励各地发展小煤窑,快速致富。那时候,开办煤窑,到县里审批即可,各级政府一路绿灯,上面还提出了鼓舞民心的“搭台唱戏”的口号,即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但最初开窑挖煤并不成气候,因为“在农村,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烧砖开窑这些与火沾边的活都损德折寿。为什么?可能与农耕传统有关系,认为这些营生大悖于春耕秋收的自然规律”,“恰恰在这时候,胡耀邦来山西,说可以利用本地资源,让乡镇企业开煤矿来发展农村经济。”山西省大小报纸广为宣传,于是,各种简陋的小煤窑在各级政府有意或无意的鼓励支持下,一拥而上。新时代的形形色色的煤老板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政府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和煤老板农民素质低下的先天性缺陷,使得这段时期的山西农村小煤窑呈现出一片混乱无序的私挖滥采状态,采空塌陷随处可见,伤亡事故频频出现。山西省政府在1987年春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才把煤矿审批权收回来,并且宣布,过去县里审批的煤矿手续全部作废,必须重新登记审查,不合格者立即关闭。
从道理上讲,省政府当然没错,然而,他们忽视了两个可怕的现实情况,一是很多煤老板都几乎是把所有的资产和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绝大多数还是负债累累,你先前红头文件批准他可以经营,现在又忽然出尔反尔,提高门槛,把他们关在财富大门之外,他们如何能够善罢甘休?不干肯定是个“死”,而且“死得”会很难看;私干有风险,但私干下去还能看见美好的希望,为什么不干呢?二是这时期的煤窑已经使得一部分人迅速暴富起来,政府的某些官员心热眼红,都已经悄悄跟各色煤老板勾结起来,以官护煤,又以煤养官。煤矿手续批不下来,他们干脆就直接私开窑口大干起来。所以,早在1990年代初,山西除过大同、潞安、阳泉、轩岗等7个国家统配矿务局、一些省直统配矿、县营矿和山西个体、乡镇等乡村煤矿达近6000处外,还至少有1万处以上的各种小黑口、小黑矿。这些乡村煤矿没有什么现代化设备,基本上靠原始的生产办法来维持,挖煤、拉煤或者建设坑道,全靠人力和畜力。设备跟不上,安全便失去了保障,于是死人、伤人现象司空见惯,每年都有或大或小数百起伤亡事故在这儿发生,其惨死在矿井下的矿工难计其数。
这段时间,由于事故频发,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连续采取了多种严厉措施,下发了各种红头文件,但说老实话,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纸上谈兵",煤老板们和那帮贪官污吏在超额利润的诱惑面前根本无法罢手,他们依然顶风作案,我行我素。直至2008年9月襄汾溃坝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的特大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才断然采取强制措施,严厉追究责任,一举罢免了山西省省长、临汾市市长和襄汾县县长等相关责任人职务,并根据违法情节的轻重不等,分别将他们移交司法机关惩处,举国为之震惊。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山西省省省长王君手握尚方宝剑,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向全省父老乡亲承诺,山西省境内的所有大小煤窑要全部整改,要彻底消灭乡镇小煤窑,还山西一个拥有蓝天、白云、青山和绿水的美好世界。这次整改不同于以往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山西矿井数由2598座压减到1053座,办矿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并责任到人,层层落实,违者严惩不贷!这等于从根源上彻底瓦解了小煤窑的生存条件。曾经在世人眼里无限风光过的数以万计的煤老板,不得不就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山西省政府这次整改遭到百般诟病,成千上万的煤老板因此血本无归,网上一度称之为“国进民退”,还有不少煤老板准备联合起诉当地政府,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山西省政府这次“缺理”“缺法”的壮举——你政府不守信誉,随便更改游戏规则,是为“缺理”;你政府不守法条,随意侵吞民营资产,是为“缺法”,还是受到绝大多数山西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毕竟,这也是山西省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无奈举动,不能为了几个煤老板的利益就再继续损害全体老百姓的利益。
百姓嘴里和媒体意义上的煤老板正在成为一个被人逐渐淡忘的历史名词。事实上,这是一个原本就不该诞生的悲情群体——他们自始至终是在做着一件损人又不利己的糊涂事儿。但不要忘了,培育出这个怪胎的是我们当地的政府。政府没有理性的短视行为,正是成千上万的煤老板能够孕育、发展,并且壮大的温床。
鲁顺民先生的《老苏》和《小经历》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翔实地记载了一个煤老板在这种大背景下生死存亡的整个过程,他以微观的笔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底层百姓经营煤业所经历过的诸多喜怒哀乐,尤其是《小经历》的这个“老苏自述”,让我们原汁原味地看到了一个煤老板的坎坷艰难、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放大了去看,这两篇文章具有相当意义上的史学资料价值,而这一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所能取代的。
相关资讯
同类文章排行
- 发往黑龙江煤矿大倾角皮带输送机整装待发
- 刮板机价格是否会随着钢材价格的变动小幅度下降?
- 嵩阳煤机建议新老煤矿用户:采购煤矿皮带输送机要认准安标
- 嵩阳煤机温馨提示煤矿用户选购刮板输送机:切勿相信工期短与超低价
- 湖北省的煤炭去产能:小煤矿的蜂拥、挣扎与衰亡
- 带式输送机厂家嵩阳煤机预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成功
- 嵩阳煤机预祝第十六届西部国际煤炭及新能源产业博览会顺利召开
- 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DSJ120/120/3*400带式输送机采购项目
- 2018第十三届榆林煤博会盛大开幕丨嵩阳煤机带式输送机资料遭疯抢
- 嵩阳煤机邀您参加第十三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
最新资讯文章
您的浏览历史


 电话:17303715996
电话:17303715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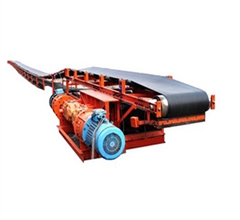



 豫公网安备 41018502000162号
豫公网安备 41018502000162号